,病发时曾有暴力倾向,经治疗后情绪趋于平稳,但社交能力退化,极少出门。母亲因担心其病情复发,对其过度保护,限制其独自外出。社区居民因对精神疾病的误解,对
社会支持理论认为,个体的社会支持网络包括正式支持(如政府、机构、社区组织等)和非正式支持(如家庭、亲友、邻里等),良好的支持网络能帮助个体应对困境、提升适应能力。对周某的评估如下:
(1)非正式支持薄弱:家庭支持存在“过度保护”问题,母亲的限制反而加剧其社交退缩;缺乏亲友、邻里支持,因疾病标签被孤立。
(2)正式支持不足:虽享受低保和医疗救助,但社区提供的康复服务单一,仅停留在定期随访层面,缺乏针对性的社交训练和就业支持。
(3)个体层面障碍:长期封闭导致社交技能退化,自我认同感低,对社区环境存在恐惧心理,缺乏融入动力。
(4)环境层面障碍:社区居民对精神疾病认知不足,存在偏见和歧视,公共空间缺乏包容的氛围。
以社会支持理论为核心,通过构建“家庭-社区-机构”三维支持网络,整合正式与非正式资源,帮助周某重建社会连接,提升社区融入能力。
1.短期目标:改善家庭支持模式,减少过度保护;协助周某完成3次社区内低强度社交(如参与社区便民活动)。
2.中期目标:链接社区资源,为周某提供1次技能培训(如手工制作);建立2-3个稳定的同辈支持关系。
3.长期目标:周某能自主参与社区常规活动,获得社区居民的接纳;掌握基本社交技能,提升自我价值感。
1.家庭支持优化:通过家庭治疗,引导母亲调整保护方式,学习“适度放手”;邀请母亲参与精神疾病康复知识讲座,减少对病情复发的过度焦虑。
2.非正式支持重建:组织社区内有相似经历的康复者成立“同伴支持小组”,每周开展1次分享会,让周某在同辈中获得归属感;动员热心邻里定期探访,从简单问候逐步过渡到共同参与活动。
3.正式支持整合:链接社区服务中心,为周某提供社交技能训练课程(每周2次);协调社区手工坊,为其提供免费技能培训,帮助其制作简单手工艺品。
4.社区环境营造:在社区开展精神健康知识宣传活动(如摆摊宣传、发放手册),邀请周某作为“康复者代表”分享经历(视其状态而定),减少居民偏见。

每周入户探访2次,以周某感兴趣的话题(如历史故事)为切入点,建立信任关系。
与母亲进行3次单独沟通,通过案例分享说明过度保护的负面影响,共同制定“逐步放手”计划(如先允许周某在小区内独自散步10分钟,逐步延长时间)。
链接心理咨询师为家庭提供1次康复指导,解答周某关于病情复发的担忧以及未来人生规划。

邀请周某加入社区“康复者同伴小组”,初期由社工陪同参与,鼓励其倾听他人分享,逐步引导其表达自己的感受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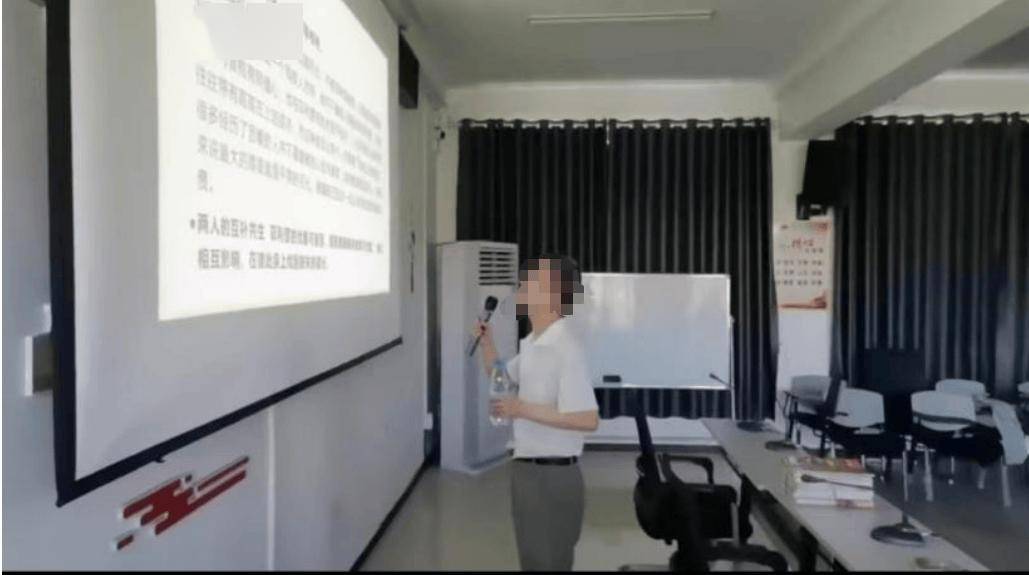
组织小组成员共同参与社区“心灵光影,共读时光”读书会活动,让周某在分享观后感的过程中获得成就感,同时与同伴建立互动。
针对周某的社交恐惧,开展5次一对一社交技能训练,模拟“邻里打招呼”“商店购物”等场景,提升其沟通能力。

安排周某参加社区手工坊的编织、烘焙等培训,每周2次,由社工协助其完成简单作品(如制作蛋挞、饼干等),并在社区便民日展示销售,增强其自我价值感。

联合社区居委会开展“精神健康知识进楼栋”活动,周某主动提出帮忙分发宣传册,过程中获得多位居民的肯定。
鼓励母亲参与社区“家属互助会”,与其他家长交流经验,减轻其心理压力,使其更放心让周某参与社区活动。
周某已能独立参加同伴小组活动,并主动邀请小组成员到家中做客,母亲反馈其“脸上笑容多了”。周某的社区归属感显著提升。
1.家庭支持模式改善:母亲不再限制周某外出,母子关系更平等,母亲表示“看到他能自己做事,我也松了口气”。
2.社交网络重建:周某与3名同伴建立稳定联系,能主动与邻里打招呼,参与社区活动的频率从每月1次提升至每周2-3次。
自我价值提升:通过手工制作获得认同感,周某表示“觉得自己不是没用的人了”,焦虑情绪明显减少。
3.社区环境优化:经宣传活动后,80%的受访居民表示“愿意接纳康复者”,社区包容氛围初步形成。
1.精神残障人士的社区融入需“内外兼修”,既要提升个体能力,也要优化外部支持网络,二者缺一不可。
2.家庭支持是关键但需“适度”,过度保护或忽视都会阻碍融入,社工需引导家庭找到平衡。
3.同伴支持的作用不可替代,康复者之间的共情能有效降低社交恐惧,未来可扩大同伴小组规模,形成长效机制。
4.社区环境的改变需要长期努力,应将精神健康宣传纳入社区常规工作,从根源上消除偏见。
通过构建多元社会支持网络,周某逐步打破了“自我封闭-社区排斥”的恶性循环,证明社会支持视角下的介入能有效推动精神残疾人的社区融入,为同类群体的服务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。